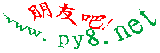我的人生当中,有一个人的债务无法偿还,那就是母亲……
我的母亲出生于1931年,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的故乡,原高邮县的武宁乡(今合并三垛镇)一个地主家族。新中国成立后,风华正茂青春活力的她,却遭遇人生最大的不幸,母亲的父母因成份问题经常遭批斗,先后含冤撒手人寰。她自己也因此受到株连和世人的冷嘲热讽。
为了生计, 她身心交瘁地来到高邮城“帮人”(注:帮人是旧社会到刚刚解放时高邮的地方土语。指的是贫穷落迫的人给有钱有势的人家做杂事,比现在“保姆”的身份还要低下,若做不好事情直接要被打骂或解雇的。),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
后来,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。1965年,35岁的母亲怀上我,当时爸爸还不相信,将信将疑地说“铁树还开花……”。可母亲腹中怀着我,每天与正常人一样做工,一直干到分娩。身为大龄产妇,母亲生我竟然没去医院。据说我胎盘大,母亲默默地强忍巨痛,一声不吭咬破了舌头,疼了一整夜才产下了我。
我11岁春季时,农村落后没有浴室,我便与几个孩童到高邮南门的红星浴室沐浴,刚进管绎巷,(今盂城绎处),突然蹿出一条大狼狗,吓得我惊慌失措,说时迟,那时快,一辆装满土坯的农用拖拉机从我身上穿过,或许是菩萨显灵保佑,我竟然没有被压碎身亡!当时母亲听到这个坏消息,她睡在地上打滚,痛哭流涕,浑身是泥巴的母亲又和父亲赶赴事故现场,与肇事者理论,当时也没有什么交警大队,无法进行“事故认定”,母亲为了我竟想“寻短见”决定与对方拼个“鱼死网破”。
在母亲的艰辛努力下,人家终于答应给我看病。我被诊断为“膝盖骨裂”。那时候高邮三垛镇医院有姓许的女医生,此人看上去40多岁,脸上有麻子,因医术高明,扬州地区有好多的伤员前来就治。为了省钱治疗,母亲只好背着瘸腿的我,步行三垛,一背就是25公里,每次背着大个子的我,母亲步履维艰地前行,衣襟都全部湿透,通红的脸颊上豆大的汗珠往往下滴。
记忆中的母亲相貌青瘦,身穿布衣,脸皮褐色,平素木讷少言,但多舛的命运练就了她不向命运屈服低头的性格,史无前例的年代,物质匮乏,家中柴禾缺乏,母亲不仅每天要做工养活我,还要起早赶赴上河(今高邮镇王港闸)拾草,那时我有八、九岁了,依稀记得母亲凌晨两点钟就到十多公里的上河拾柴禾。拾一担草回来,家中可以生火,有时母亲拾草,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,将草抢走,可倔强的母亲就是抓着草不放,有时还被人家挨打受辱。
1980年5月上旬,生长农村的我被县体委抽调集训,备战扬州市中学生篮球运动会。由于当时的武安初中转入高邮县中学读书,这对于酷爱篮球运动的我,喜从天降。
第二天,母亲为我收拾行装。一个箱子,一床绣花被子。当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子时,泪水便滴到衣服上。
“妈,你哭什么?我不在你身边,你衣服不是少洗了?再说星期天就回家了”我这一说,母亲哭得更难过了,但她没有解释为什么哭。
后来,我长大了,读懂了孟郊的 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的含意,才渐渐明白母亲当时为什么会暗自垂泪。
17岁那年,母亲意外地去世了,这让我们家承受了巨大的伤痛。在送别母亲的灵车上,我不停地抽泣,想着母亲留下的朴实话,什么“发山水淌来要人捞”、什么“桑树条子从小抈”、什么“惯儿不惯学”等等,让我感慨万端。母亲这些看似简单的口语,却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,她身上流淌中国妇女艰苦勤劳忍辱负重的母性形象就像无花的蔷薇,永不败落。
沧海桑田,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尽管每年清明节,我都要到她的坟前磕头烧纸,但没能侍奉她八年十年,我常感愧疚。活到今天的我,欠别人再多的债务,总有机会偿还。唯独欠母亲的债,今生今世也还不了,因为这是一生的感情债。